党史故事汇|1933年7月25日——记国立中山大学抗日剧社创办人洪深

1933年7月25日
——记国立中山大学抗日剧社创办人洪深
外头下了这么大的雨,可是我,注定了要在暴风雨里头找生路,我不连累你们了,我要到暴风雨里头,找我的生路去了。
——《女儿经》
可是我,告诉你们!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
——《女儿经》
个人不愿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牺牲他的生命和其他的一切吗!不会的!中国人哪一个不愿为了中国而战死!
——《募捐救济绥远民众与慰劳绥远将士缘起》
这是1933年7月25日的正午,大暑刚过,太阳以其炙烤的威能,向其下辖的万物炫耀着强权,直照得教育会礼堂前的土地寸寸龟裂出深痕,就像分裂的山河……这时树丛中阴暗的角落里,蝉正吮吸着树的汁液,而树在沉默,它向来逆来顺受,不发一言。
教育礼堂从清早到如今正午时分,人来人往,学生们进进出出,或排练剧目,或搬运道具,全为了今晚国立中山大学抗日剧社的新戏《五奎桥》。实在太热了——洪深扶正因汗水滑落些许的眼镜,示意学生们暑气过盛,略作休息,待得日头过去再搬运布置。他自己却是走到树荫下,仍要咂摸如何将李全生和周乡绅的矛盾完全地导演出来。
学生们的表演,经过了这么多时日的演练,自然是很纯熟的。只是与在上海的《五奎桥》不同,这一次的演出,不是为了展示新戏,全然是为了募集资金,支持英商太古公司海员的罢工斗争,那么,原本还算得上“温和”的《五奎桥》,还足够调动观众们的情绪吗?正值暑假,师生前来参与募捐的人数真能达到预期吗?对于这些问题,洪深心里也没有答案,他仍在翻看《五奎桥》的剧本,从上海袁牧之版的首演,到如今抗日剧社学生们的演出,《五奎桥》剧本几经推敲,已是洪深心中最得意的一部戏剧。
光影……必须多加注意,洪深想,此间条件简陋,不比在上海有欧阳山尊同志,从沉沉黑夜到天色微明,再到天光大亮,都能渐次实现,如今不是十数年前那样子了,洪深想,不是自己在上海拍摄着电影,一边从西方电影汲取艺术营养一边期待着新气象的时候了——1930年春天引进的肆意诋毁华人的美国电影《不怕死》就是一例明证,西方的电影艺术跳不出意识形态的偏见,而一无所知的国人还在歌舞升平中被歧视侵蚀着,直至家园沦丧,亡国灭种……自己愤然指出,反遭经理暴力对待,于是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呈文,历经数次开庭审理,八个月的努力,终于让大光明戏院让步认错。然而拦得住一部《不怕死》,拦得住一个“罗克”,洪深扪心自问,他拦不住所谓“艺术”,拦不住全凭利益放映电影的那些人——
是的,如今艺术已经不能仅仅是艺术,表演也不能仅仅是表演了。这时候蝉不知道为何,嚣张地用它连绵不绝的音浪包围了洪深,洪深扫视手中的剧本,正是末尾乡民在喧天的锣鼓声中,拆了那五奎桥的段落,周乡绅家族的“荣耀”,固守了百年的“风水桥”,就这样倒塌了。
然而那乡绅,那些资本家,他们真的随桥一起倒下了吗?难道,他们不是和这吮吸着大树生命的蝉一样,不仅不曾死去,还鸣叫得更大声了吗?
洪深将视线投向脚下土地龟裂的深痕,这深痕,像《五奎桥》剧目中干旱的桥东田地,像时下破碎的山河,像自己民族……饱受欺凌的现状,亟待一声声呐喊召来惊雷与甘霖,润泽它,治愈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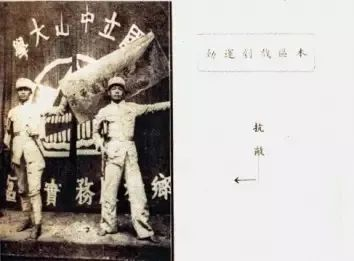
“你做的是什么官!你还是做中华民国的官呢,还是做周乡绅家的官!姓周的养一只狗,也不会像你这样听话的!”
“爹爹,他们打得你这样厉害么!”
五奎桥上,四五十人静静地听着,没有一点声息,忽然,不约而同地像暴雷似的,众人大喊一声!
“我们还等什么!拆呀!拆呀!”
礼堂内锣鼓震天价响,桥上砖石横飞,越来越多的人赶来,拆了周乡绅家这拦住了洋龙船,拦住了乡下人活路的五奎桥。
珠凤清越的声音,这时候响了起来:
“现在,乡下人有了活路了!”
“查《五奎桥》一剧,该社在第五次公演时,曾经演出,大为观众所称赞,而获得相当之成效……此次该社再次公演,定能收得更大之效果也”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当五奎桥剧目最后的锣鼓敲响,当满堂的喝彩和掌声将洪深围住,当数百元的善款从手中递交给工会联络员李五欢,洪深忽然感受到一种自我实现的喜悦,仿佛自己正被越来越大的人民的声音包围,他走出已然空无一人的深夜的剧院,蝉鸣已然停止,地面也因为降下夜露,微微润湿,此间寂静,洪深回头,又看了一眼“抗日剧社”,激动的泪洒在眼镜上。
少年时代,他曾想过“实业救国”,为此,他不辞路远,孤身在国外求学,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学成烧瓷技术,却发现此路不通,最终选择遵从一直以来内心的爱好,前往哈佛大学学习戏剧表演的艺术。
洪深也曾迷茫过“艺术”是否能够救国,因着许多文艺界“旧人”的阻拦,新戏剧的诞生,总是伴随着那样多的批评。幸好,三年前,他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友人,共同捉笔为刀,他在复旦大学,在暨南大学,在山东大学,在这里。国立中山大学,与激情洋溢的学生们、老师们,排演新话剧,他们的激情,就像五奎桥边乡民的锣鼓,能将蝉鸣压过,能将乡绅,将资本家,将欺压中国人的一切势力,都掀翻了去!
是的,在1933年7月25日的夜里,或许也是1933年7月25日的凌晨,洪深在离开“抗日剧社”的时刻,走在这条夜露凝集的路上,忽然感到他的理想,无论艺术还是民族的理想,都向他飞奔而来。刚刚回到祖国,刚开始创作自己的剧目时,他曾经写道:
“要将‘五四’以来所倡导的欧洲现代话剧,具体展现在中国舞台上……正处于由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中国话剧完成其历史性转化,奠定以后发展的基础。”
今日《五奎桥》的成功演出,让洪深吃下了逐梦途中的定心丸:对艺术的追求与对家国的热爱不必抽离,他完全可以一边与拥抱戏剧的魅力,一边投身于唤醒大众、救国救民的崇高事业。
抗日剧社的公演,这次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1933年的夏天结束前,洪深还会带领学生们,一直演下去,直到趴伏在中华民族参天大树的每一个蛀虫生命都走到尽头的那一天。
1933年7月25日,国立中山大学抗日剧社的第五次公演,结束了。

“本校抗日剧社,自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两日举行第五次公演以后,已有数月之久,近值学校开学之期,特于九月九日举行第六次大公演,节目现已决定为洪深之《五奎桥》……各校号房及各大书局代售之入场券,购买者亦极为踊跃云”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33年7月25日,这天之后,《五奎桥》就将随洪深教授一起,永远地留在中山大学的记忆里,成为一抹鲜明的红色印痕。
人物档案

中山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生卒年月:1894-1955
剧作家、导演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中国电影、话剧的开拓者,抗战文艺先锋战士


